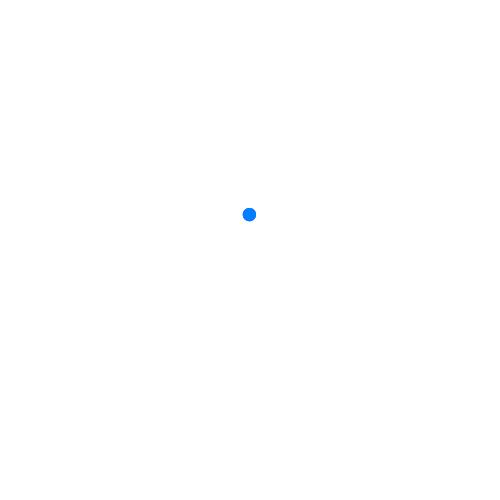离职证明内容不符合有关规定 法院判令公司为职工重新出具离职证明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许灿(化名)在公司工作时间长、工作岗位亦有变化,公司为他出具的离职证明虽具备相应的内容但没有反映其主要任职经历,因此,他认为该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要求公司重新为其出具。而公司以法律没有规定离职证明必须体现其所有履历、无需载明每一份劳动合同签订的起始和结束日期为由予以拒绝。为此,双方形成争议。
二审法院认为,离职证明除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终结外,亦有证明劳动者工作经历、专业技能之功用。虽然许灿在劳动合同解除时未从事质量控制主管工作,但其在公司长期担任该职务,仅在离职前一年调岗至高级质量控制员岗位,如公司仅在离职证明中列明其离职前工作岗位,难以全面反映其实际工作经验、岗位工作能力,故于12月22终审判令公司重新出具离职证明。
离职证明内容存疑
职工要求重新出具
2014年4月1日,公司与许灿签订首份劳动合同且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其在服装质量检验部门担任质量控制主管职务。而在此前的2014年3月28日,公司与他及外服公司签订三方《工龄承认补充协议》,约定公司承认其通过外服公司自2000年10月1日起被派遣至公司工作期间的连续工龄。
2021年12月29日,公司向许灿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该通知载明:因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许灿所在的高级质量控制员岗位已无法继续维持,决定予以取消;同时,通知其2021年12月31日解除双方间的劳动合同。
许灿于2022年1月8日收到的离职证明载明:“兹证明许灿自2000年10月1日加入我司,离职时担任高级质量控制员(英文)职位。由于业务整合的原因经公司决定停止部门所有业务。最后工作日为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22日,许灿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公司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并支付延误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离职证明对本人重新就业权益的损害,赔偿金额从离职当日起至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履行日每月3万元。
由于仲裁机构不予受理,许灿起诉至一审法院。

应当如何出具证明
争议双方各执一词
许灿诉称,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内容存在以下显著错误:
一是未写明劳动合同期限。
二是工作岗位写为“离职时担任高级质量控制员(英文)”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工作岗位。公司仅以人事管理截图作为其工作岗位的证据,而该证据是公司单方面自行制作或杜撰的非公开内容,且未经认证翻译,形式不合法,内容不真实,不能证明公司在离职证明上载明的许灿离职时工作岗位。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变更劳动合同工作岗位的约定。
三是工作年限写为“自2000年10月1日加入我司”缺乏事实依据。公司以找不到资料为由,不出示作为用人单位本应掌握的许灿入职信息材料相关的直接证据,仅以《工龄承认补充协议》作为其入职时间的证据,但该证据只可证明许灿与外服公司的劳动关系起始时间,无法排除其在此之前已经入职公司的可能性,不符合排他性原则。
四是附加的非法定内容“由于业务整合的原因经公司决定停止部门所有业务”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公司辩称,职工的岗位变更时有发生,并无法律规定离职证明必须体现其所有履历。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是公司适用于所有职工的标准版本,不载明劳动合同的起始和每一份劳动合同签订的起始和结束日期,但是会写明加入公司和最后的工作日,以方便离职的员工开展下一次的就业。公司已依法向许灿出具了真实客观的离职证明,充分履行了用人单位的义务,不应向其支付任何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上载明许灿的入职日期及劳动合同解除前的岗位,相关内容与其在公司实际工作履历情况并没有出入之处,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已经履行了向劳动者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法定义务,故判决驳回许灿的全部诉讼请求。
证明内容确有不妥
公司应当予以纠正
许灿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针对许灿的请求分析如下:
关于劳动合同期限,依据已查明事实,许灿于2014年3月28日方首次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自2014年4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在此之前,许灿系通过外服公司派遣至公司工作,对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规定,许灿要求在离职证明中写明其劳动合同期限,确有依据。
关于工作岗位,公司就许灿原所处质量控制主管岗位已撤销、许灿的职位变更为高级质量控制员之主张提供了董事会决议、电子邮件等证据,许灿虽对此持有异议,但依据许灿申请仲裁提出恢复劳动合同约定的原岗位之请求、仲裁机构决定不予受理等事实,实难认定其自2020年8月3日起仍从事质量控制主管工作。
但是,从《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对离职证明法定内容之设置看,相关证明除证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之终结外,亦有证明劳动者工作经历、专业技能之功用。虽然许灿在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时未从事质量控制主管岗位工作,但从其在公司的工作经历看,其长期担任质量控制主管,在离职前调岗至高级质量控制员岗位仅一年余,如公司仅在离职证明中列明其离职前工作岗位,难以全面反映其实际工作经验、岗位工作能力。同时,公司系我国境内企业,我国通用文字为规范汉字,在许灿持有异议的情况下,公司仅以英文名称列明许灿岗位,亦有不妥。故就本案实际情况而言,公司应在离职证明即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以规范汉字写明许灿包括质量控制主管在内的工作岗位经历。
关于许灿在公司的入职时间,依据其所述的2000年10月1日前后之工作单位及在案证据,实难认定其所称的1995年8月1日至2000年9月30日工作经历属于离职证明应写明的本单位工作年限范畴,故对其该异议,二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许灿对离职证明中所载“由于业务整合的原因经公司决定停止部门所有业务”之异议,公司在离职证明中写明离职原因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亦难以认定该内容对许灿产生不利影响,但结合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的实际用途以及《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15条有关用人单位出具的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应写明劳动合同期限、终止或解除的日期、所担任的工作”“如果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可在证明中客观地说明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之规定,在许灿所述有异议情况下,公司不宜写入相关内容为妥。
综上,二审法院认为,许灿主张的经济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其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据查明的事实,判决撤销原判,由公司向许灿出具符合法律规定的离职证明。
本报记者 赵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