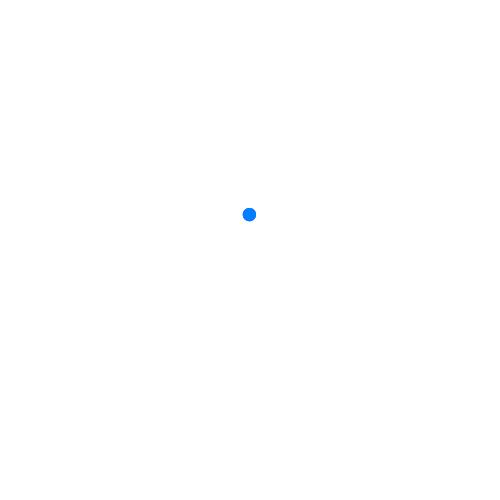3600 元育儿补贴,如何“拯救”生育率?

2024年,我国人口总数为14.08亿人,较上一年下降139万人,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下降,人口形势可谓严峻[1]。
而依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中方案的估计,我国未来人口还将继续减少,在2050年下降到12.7亿左右,在2100年下降到6.4亿[2]。
当人口持续负增长,少子化、老龄化压力加剧,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开始陆续出台。从逐步放宽的生育限制到首次实施的现金补贴,“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向生育友好型社会迈进。
在此过程中,哪些政策最能有效刺激生育?每年3600元现金补贴起到了何种作用?各国的生育政策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启发?我们尝试探究并回答这些问题。

01 重压之下,生育支持政策持续加码
人口负增长已经构成了我国中长期人口变化的主轴,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人口相关的问题:“低生育率陷阱”、人口老龄化、现收现付的保障体系面临压力等。而过去二孩、三孩等人口政策的经验也在提醒我们,仅仅放开生育子女个数的限制并不能扭转人口负增长的趋势,还需要更多的激励。
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呈现,即为育龄人群、婴幼儿和照护者提供经济、服务、就业等多方面支持,并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目标[3]。
2024年,国家明确将生育支持措施归纳为经济、服务、时间和文化四方面,推动其向更加系统化、结构化的方向发展[3]。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各地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支持生育。四川攀枝花、湖南长沙等几十个城市发放了不同额度的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广东中山、湖北武汉等地企业设置“生育友好岗”,方便父母兼顾家庭与工作;此外还有上海、河北衡水等多地在不断完善普惠性托育服务,让家长“放心托,托得起”[4]。
而一项关于“生育支持政策预期效果对育龄人群生育计划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在各种生育支持政策中,育儿补贴是大多育龄人群认为能产生实际效果的政策 [5]。
今年7月,《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正式公布,自2025年1月1日起每个符合法律法规生育的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可获得3600元补贴[6]。
从宏观来看,过去三年总共有约2800万新出生人口,若每人每年领取3600元,则每年大概要发放1000亿补贴[7]。在长期低迷的生育态势下,这一政策的作用在哪里?1000亿补贴分摊到每个家庭,又能起多大效果?
02 一年3600元补贴,有什么作用
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3600元育儿补贴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对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两个家庭进行了访谈。
在农村全职带娃的徐星表示,一年3600元的补贴虽然无法彻底解除育儿的经济压力,但也算得上是“及时雨”,能够覆盖部分高频的刚需支出。
而对于家庭经济状况尚可的王明来说,除了纸尿裤、奶粉等必需品,他们还会给孩子提供额外的托育、医疗等服务,比起实际的购买力,政策带来的更多是情绪价值和社会认同,是对他们在育儿过程中付出的心血与成本的认可。
徐星和王明家庭的差异并非个例,从全国不同可支配收入群体分布来看,我们更能看清其中的差距。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城镇前20%的高收入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3763元,农村最低20%的家庭仅有5410元,相差10万有余[7]。这也意味着,对于可支配收入偏低的家庭来说,3600元的育儿补贴切切实实能帮助他们抚养新生儿。
在具体用途上,3600元若全部用于婴幼儿护理,可购置大约一年所需的帮宝适、babycare等品牌拉拉裤,而如果选择更经济的品牌,能直接覆盖掉孩子三年的拉拉裤费用;若优先保障营养,则能承担约3个月的奶粉费用。

然而,在期待政策落地的同时,也有一些父母存在顾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国家发放补贴后,商家会不会趁机涨价?
被访者徐星就有同样的担忧,有母婴店店员告诉她,政策出台后某奶粉月均贵了约200元,纸尿裤也略有上涨。我们通过查询电商平台历史价格,徐星所提到的品牌产品在天猫国际商城并未出现明显调价,目前尚不能断定涨价是否会成为趋势。
大家的讨论与忧虑反映出育儿成本既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也离不开更稳定的物价环境与市场监督机制。未来若能进一步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同步根据家庭收入差异细化补贴标准,这份育儿补贴才能更精准地惠及每个需要的家庭,为更多父母减轻育儿压力。
03 哪些政策,能有效刺激生育
要想真正提升生育率,育儿补贴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还需要更多元、更完善的政策配套支持。不少地区此前就已推出多种补贴或服务,推动“政策红包”更具可持续性和实效性。我们选取了部分城市,看看他们在稳住和提升生育率上,都做了什么。
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湖北天门和上海是近些年生育率增长较快的典型城市,两地的策略各有侧重。直接的高额经济激励(二孩每月补贴800元,三孩每月补贴1000元,一直发到3周岁)、强效的政策执行机制和融入发展大局的顶层设计是湖北天门的“三大秘诀”,推动天门市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长17%,实现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8]。
而上海则更注重托育服务的提供,不仅有近1500家托育机构,还为1-3岁幼儿免费提供一定次数的“家门口”临时托育服务,减轻了女性“脱产带娃”的压力 [4]。

相比之下,一些长期以来生育率较高的城市(如广东佛山、福建厦门),在“多子多福”的传统之外,还有着更为全面的生育支持体系,通过经济补贴、医疗设施、托育服务等多维服务降低人们生育的后顾之忧。
从短期的刺激生育,到长远的稳定高生育率,这些城市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而放眼国际,在生育政治、生育体系资金投入和孕产护理文化三个不同因素多重作用下,各国生育政策的侧重与实现路径又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可分为公共政策引导型和市场自由调节型两种机制[9]。
公共政策引导型指通过公共财政投入和调节来保障生育,需要政府持续且高额的资金支持,其典型代表是瑞典。早在20世纪70年代,瑞典政府就大力发展公共托育服务和父母育儿假政策。瑞典父母生育子女后,可享受480天育儿假,加上父亲“配额”制度的实施,确保男性劳动者的育儿参与,将育儿责任从“女性天职”转向“父母共同义务”[9]。
经过几十年的政策努力,瑞典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30%提升至70%以上,不足3%的公共托育率也增至90%以上,生育率在发达国家中也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10]。

相比之下,市场自由调节型没有政府过多的政策干预,而依靠企业提供的“工作福利”,其典型代表是美国。这种基于市场调节的筛选机制,实际牺牲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来提高留在劳动力市场上高技能女性的就业质量。
因此,美国政府对家庭的支持局限于低收入和弱势群体,如美国的“开端计划”主要为低收入家庭5岁儿童提供照顾和早教服务,育有子女的收入贫困家庭,可以获得政府的现金援助[9]。
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则介于二者之间,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借助市场力量,关注女性的就业问题。针对职业中断女性,2010年韩国就颁布了《职业中断女性再就业促进法》,鼓励企业组织培训、开展就业实习项目[11]。
在实践中,多国政府还意识到鼓励“代际照料”的重要性,如日本为鼓励代际支持,政府与企业合作,逐渐推出“老人给孙子孙女’交学费‘不用缴税”政策和“带孙子假”;韩国实行“照看孙子辈项目”,由政府向照顾孙子和孙女的祖母或外祖母提供津贴。这些经验虽然没有大幅提升日本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但对降幅也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11]。
生育不是个人的责任,也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决定”,而是“整个社会的选择”。从职场歧视到制度保障,从家庭承压到社会共担,从个体焦虑到系统支撑,每走一步,我们距离生育友好型社会就更近一点。
3600元的全国性育儿补贴不是生育支持的终点,未来还需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改善职场文化、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系统性地降低育龄人口的生育焦虑,让大家生得起,也养得好。